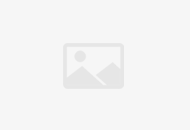雄鸡一唱天下白 下一句是什么 莫言散文中的
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
《旧“创作谈”批判》
然后心平气和休息片刻,思绪开始如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天上人间,古今中外,坟中枯骨,松下幽灵,公子王孙,才子佳人,穷山恶水,刁民泼妇,枯藤昏鸦,古道瘦马,高山流水,大浪淘沙,鸡鸣狗叫,鹅行鸭步——把各种意象叠加起来,翻来覆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
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招,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如果非要统一,多半会装腔作势牛头马面虚情假意。因为有许多东西是说不清也道不白的。当头擂你一狼牙棒,请问哪里是痛点?
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支撑作品脊梁的,必须是也不会不是作家那点点灵气。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作,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主题先行,也未必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先有主题,后编故事,而且编得有鼻子有眼睛,连眼睫毛都会打呼扇,这也是一种大本事。文学应该百无禁忌(特定意义),应该大胆地凌云健笔,在荒诞中说出的道理也许不荒诞,犹如酒后吐真言。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应该有点邪劲儿。敲锣卖糖,咱们各干一行。你是仙音绕梁三月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不是我的福气?
也可以超脱时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也可以去描绘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也可以去勾勒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泼墨大写意,留白题小诗;画一个朗朗乾坤花花世界给人看。
有了这样的本事不愁进不了文学的小屋。
当时毕竟是年轻气盛,口出狂言,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必须准备承受一切由此产生的麻烦。今日重读此文,竟有隔世之感。想想当年,无论如何也是浅薄,写这类宣言书一样的东西其实与文学无半点裨益,只能给人留下狂妄自大的不良印象。因为说到底,文学不是体育竞赛,谁跟谁过不去呢?作家其实是命定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并没有多少意义。这篇文章的大毛病就是张牙舞爪,偏激则偏激矣,深刻却是一点也没有。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把它当成自己创作的指南。写什么,怎样写,只有上帝知道吧?我向来认为创作谈之类万万不能信,谁信了谁就会误入歧途。我后来只相信梦境,只相信小说就是梦境的记录。前几天翻阅《西北军事文学》,见彩色插页上有西北画家潘丁丁一幅题为《天马》的水粉画,有两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有无数匹曲颈如天鹅的天马,整幅画传达出一种禅的味道:非常静谧,非常灵动,是静与动的和谐统一,是梦与现实的交融,这样的才是好的天马呢。1985年,稍微清醒了一点,痛感到骚乱过后的蚀骨凄凉。为《青年文学》写了一篇小说,同时又附了一篇创作谈:小说写到如今,我个人感觉到几近黔驴技穷,虽跳踢叫嚷,技实穷矣!去年《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读者见面,无疑是极大地开阔了许多不懂外文的作家们的眼界,面对巨著产生的惶恐和惶恐过后的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蠢蠢欲动的自然后果是使这两年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类魔幻和魔幻的变奏,大量标点符号的省略和几种不同字体的变奏。从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国作家的喜剧,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剧。事情的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家具有出类拔萃的模仿能力和群起效尤的可贵热情。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家们的消化不良和囫囵吞枣的牺牲精神。本人自在受害者之列。我现在恨不得飞跑着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是两座灼热的火炉子,我们多么像冰块。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光明,洞烛自己的黑暗就尽够了,万不可太靠前。这其实是流行真理,说个不休是因为我的浅薄。中国人向以宽容待人为美德,不酷评别人也就免去了别人对自己的酷评……因为高级一点的中国人除了宽容的美德之外还有睚眦必报的美德,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少说话总是能比较得便宜。当然我内心里总希望作家能像凶猛的狼一样互相咬得血肉模糊,评论家像勇敢的狗一样互相撕得脱毛裂皮,评论家和作家像狗和狼一样咬得花开鸟鸣,形成一种激烈生动的咬进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咬进既然无法实行,大家就该互相宽容,不但宽容别人,而且宽容自己。我们拜倒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脚下,虽然显得少骨头,但崇拜伟人是人类的通俗感情,故而应该宽容;我们不去学人家的精髓而去学人家的皮毛,虽然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天真可爱,但仿造的枪炮也可以杀人故而也应该宽容,我们以中国的魔幻与拉美的魔幻争高低,虽然是一种准阿Q精神,但毕竟形象地说明了外国有的我们也有而且早就有了从而唤起一种眷恋伟大民族文化的高尚情操,不但故而也在宽容之列,甚至应给予某些适当的奖励啦。但宽容是有限度的,对别人对自己都是。在充分宽容之后,真该想想小说该怎样写了。
伟大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财富,我认为不是坐着床单升天之类诡奇的细节,也不是长达一千字的句子,这些好像都是雕虫小技。伟大作品毫无疑问是伟大灵魂的独特的陌生的运动轨迹的记录,由于轨迹的奇异,作家灵魂的烛光就照亮了没被别的烛光照亮过的黑暗。马尔克斯的时空意识与我们一样吗?海明威的爱情观与福克纳一样吗?卡夫卡的人生观与萨特的人生观一样吗?他们的思想当然可以有我们给人家贴上进步或是反动的标签,但他们的作品呢?我觉得小说作美给人看,而只要传达了真情实感的就具有了相当充分的没美的因素。我觉得小说越来越变为人类情绪的容器,故事、语言、人物,都是制造这容器的材料。所以,衡量小说的终极标准,应该是小说里包容着的人类的——当然是打上了时代烙印、富有民族特色、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统一的——情绪。
《草鞋窨子》是个处在伪小说与真小说之间的东西,它除了说明在寒冷的冬天人钻进地洞能够得到一些温暖,除了说明鬼怪神异对人的警示作用,究竟传递了、包容了多少人类的情绪呢?
这种草鞋窨子在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它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是:贫困+优雅。
这篇破文章还有些意思,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妙不妙就是。怎样才能抄了别人又不让别人看出痕迹呢?这只能靠自己琢磨。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技巧都不很复杂。怎样让鸡蛋立起来呢?打破就立起来了——十分简单。相信好运气的人都能碰到这种“一破而立”的机会。
又有,凡人都是有些坏毛病的,所以除了互相吹捧之外还有互相攻击,真正拿出艺术良心来评判仇敌作品的人古来也有,只是数量少些罢了。现今在地方作家群里还好,军队的作家们则全都如乌眼鸡般乱啄,果然是革命军人斗志昂扬,算啦,还能活几天呢?“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何况几个阉骡子般的臭文人呢?最无能的人才来写小说,当然首先是说我自己。
转眼到了1986年,《红高粱》使我走了点红,《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红高粱》,嘱我做创作谈,转载小说是令我愉快的事,写创作谈是让我痛苦的事,但还是没话找话说地写了一篇:
十年一觉高粱梦从小在黑土里打滚,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砍高粱秸子、剪高粱穗子,吃高粱米、拉高粱屎、做高粱梦,满脑袋高粱花子,写红高粱。所以我爱极了红高粱,所以我恨透了红高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那个公社的书记,从海南岛弄来了一种杂交高粱,产量特别高,但是味道苦涩,公鸡吃了不打鸣,母鸡吃了不下蛋。人吃了便秘。乡村干部去公社诉苦,书记发明了一个办法,让大家回去用肉汤泡着吃。这法子太贵族,无法实行,书记就到医院蹲点,与医院的三结合攻关小组研究出了一种的确有效而且方便实行的方法,那就是,每吃一个杂交高粱面窝头,就吃两粒炒熟的蓖麻籽。这法子廉价而且有效,于是一夜之间就推行开来。但带来的问题也还是不少,这里就不去多说了。“文革”十年,我在农村,吃了足有三千斤杂交高粱,所以一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就想:去你妈的杂交高粱,这一下老子不用吃你啦!在“文革”的十年里,我们十分地怀念那种好吃也好看的纯种的红高粱。我认为一个作家——何止是作家呢——一个人最宝贵的素质就是能够不断地回忆往昔。往昔就是历史,历史是春天里的冬天,秋天里的夏天,夏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秋天。秋天,我坐在一条高高的河堤上,看着堤岸下的柳树把一片片细眉般的黄叶抛掷到水面上,黄叶就在瓦蓝的水面上缓缓漂流,那时候,我的眼前就腾起了一阵阵轻烟般的薄雾,在薄雾中出现一条条纵横交错、通往过去的羊肠小路。沿着这些小路往前走,无数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甜蜜恋爱过、辛勤劳动过、英勇斗争过、自相残杀过的人们,一个个与我相遇。他们急急忙忙地向我诉说,他们认认真真地为我表演,他们哭、笑、忧、惧、骂、打,他们播种、收获、偷情做爱、生儿育女……幻想再现历史……追忆逝去岁月,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最近,我比较认真地回顾了我几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核心,是我对自己的童年生活的追忆。这是一曲忧郁的为了埋葬自己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了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红高粱》是我修建的另一座坟墓的第一块基石。在这座坟墓里,将埋葬1921-1958年间,我的故乡一部分乡亲的灵魂。我希望这座坟墓是恢弘的、辉煌的,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我希望能镌刻上一株红高粱,我希望这株红高粱能成为我的父老乡亲们伟大灵魂的象征。
《红高粱》是在比较意义上超越了我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的作品,我的记忆跨过了自我的门槛,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那里就是浩瀚如海、辉煌如血的高粱世界。
郑万隆提出过“第三种生活”的概念,我进入的高粱世界就是“第三种生活”。
我的“第三世界”是在我种过高粱、吃过高粱的基础上,是在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喝过高粱酒后讲的高粱话的基础上,加上了我的高粱想象力后捣鼓出来的。
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系列就是扎根文学。我的根只能扎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里。我爱这块黑土就是爱祖国,爱这块黑土就是爱人民。本文开头提到“杂交高粱”,之所以提到这个狗杂种,是因为我想到,对土地——乡土的热爱,绝对不能盲目。爱的第一要义就是残酷地批判,否则就会因为理智的蒙蔽,导致残酷的游戏。我准备用十年时间做一场高粱梦。十年一觉高粱梦。果然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到了1987年,我便由红变黑,先是《欢乐》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红蝗》被人狗头淋血,不但仇敌恨我,连那些好哥们儿也龇牙咧嘴了。这才进入了好的状态。能写出遭人骂的文章比写出让人夸的文章是更大的欣慰。我相信在我的面前还有路。因为有上帝的指引,因为我知道我半是野兽
半是人,所以我还能往前走。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好作家们,其实是一些不可救药的王八蛋。他们的”文学“只能是那种东西。现在什么是我的文学观呢?……它在变化、发展、一圈一圈地旋转着。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吧——这就是文学!
重读前年对“旧创作谈”的批评,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在北京随地解溲是要被罚款的,但人真要坏就应该坏透了气才妙。在墙角撒尿是野狗的行为,但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却变成了英雄的壮举。上帝也怕野种和无赖,譬如孙悟空,无赖泼皮极端,在天宫里胡作非为,上帝也只好招安他。小说家的上帝,大概是一些“小说创作法则”之类的东西,滋一些尿在上边,可能有利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呢。批判过后,又是五年过去了,1987-1992,大概是新时期文学由辉煌走向暗淡的一段凄凉岁月,但我很快就习惯了,习惯暗淡比习惯辉煌更容易。习惯了之后,我觉得清冷的小说世界比前几年的热闹更有趣也更正常。文学毕竟不是靠起哄和闹秧子就能出名堂的。在众多兄弟扬言下海捞大钱的喧闹声中,我还是坚定不移地靠写小说混饭,自我感觉还不错,回头检点一下,成绩虽然不大,但还是小有收获。首先,经过了几次操练之后,我对如何写作长篇小说心里有了数,意识到当年在《红高粱家族》后记中所说的“长篇无非就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言”的“长篇小说理论”几乎是胡言乱语。我感到长篇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也最难解决的就是结构。当然,这也是别人说过的话,我不过是有很深的同感罢了。在我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和《酒国》里,我做了三次不同的尝试,自认为基本上没有东施效颦,新东西虽然不多,但是有。我看到一些有眼光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不由得喜上心头。
我原来是想在1990年前把《红高粱家族》的故事用一百万字讲完的,但很多临时冒出来的念头促使我写了一百万与红高粱家族无关的文章,这也许是福,也许是祸,而是福是祸都是命运使然,想躲也躲不过去。
技巧熟练,并不总是成就一部大作品的根本原因。有一些评论家总是怀念我的《透明的红萝卜》,认为我后来的作品不好,我个人很难同意这种判断,有眼光的读者也不这样看。
收到这个集子(《怀抱鲜花的女人》)里的,是我这两年里写的六个中篇,自我感觉良好,产生良好感觉的主要理由是:它们各有特点,而且都有很强的故事性。
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当然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了。
河水只有流动着才能新鲜,观念只有变化着才有活力,如果我能不断地批判自己的文学观,我的小说就可能常有新鲜的气息。我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于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能不能不赶潮头凑热闹,则基本是做人的原则,对写小说的法则影响不大。其实写小说也很难有什么一定的法则。就像很多先生说过的那样:我的下一部小说将是最好的。是不是真好很难说,但这点心劲儿还是得有,这也是小说师傅们不断演练的动力。
既然是创作谈,总要说几句小说观念的话,总要说几句我目前的小说观念。前边所说的“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虽然具体,但不太玄虚也就不“哲学”,显得我很没有水平似的,这不行,要把自己显得好像有点水平才好。于是就把前年为小说集《白棉花》作的序言剪贴在后:难以捕捉的幽灵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好小说的样子,它像一团火滚来滚去,它像一股水涌来涌去,它像一只遍体辉煌的大鸟飞来飞去……我不停地追逐着,有好几次
兴奋地感觉到已经牢牢地逮住了它,但一觉醒来,立即又糊涂了。好小说的模样在梦中我可以描述,但清醒时却难著一言。除了必要的条件之外,逮住好小说太靠运气了。我连做梦都想着写出好的小说,可我始终未写出在我的梦中看到过的那种像火像水又像飞鸟的小说。我一直在努力逮住它。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是我努力的记录。没逮住,但揪下了它几根羽毛。在努力中等待好运气。好的小说就像幽灵一样。有朝一日让我逮住你……也许我永远逮不住你……我总有一天要逮住你……冷静点,我。这就是我最新的小说观了。我预感到逮住一部好小说的时机即将到来。孩儿们,拼了吧!
三年后补记于此。
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全诗
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全诗如下: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作品出处】出自《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毛泽东于1950年10月所做的一首词。该作品是新中国建国一周年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全国各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欢聚向毛泽东及其他党、政、军领导人献礼、献旗,以表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作品原文】浣溪沙①·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②天,百年魔怪舞翩跹④,人民五亿⑤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⑥,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⑦更无前。【作品注释】①浣溪沙:词牌名,唐教坊(音乐学校)里曲子的名称。②赤县:指中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介绍战国末驺(zou邹)衍的说法: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③百年魔怪舞翩跹: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起,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他们和他们的走狗在中国横行霸道,好似群魔乱舞。④人民五亿:五亿各族人民。⑤一唱雄鸡天下白:此句是由“雄鸡一声天下白”演变过来的,出自唐代诗人李贺的《致酒行》。原句为: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⑥于阗:新疆吾维尔自治区西南部县名,1959年改于田。当地人民以能歌善舞著名。这里借指新疆文工团所表演的音乐歌舞节目。万方:古人称国族为方,《易经》有"鬼方"。乐奏: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误植为《奏乐》。⑦兴会:兴致、兴趣。【作品译文】旧中国的天黑夜茫茫,一百年来妖魔鬼怪肆意狂欢,五亿各族人民却无法团圆。雄鸡终于高鸣祖国得了光明,东西南北尽歌舞其中还有新疆人,诗人们欣喜唱和兴致无边。【创作背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民族人民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之际,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10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典,全国158名各族人民代表欢聚一堂,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献礼大会,各民族文工团表演了歌舞节目,毛泽东与柳亚子先生同席观看了歌舞晚会。柳亚子在毛主席的鼓动下,即兴赋《浣溪沙》一首赠予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又步韵和了这首词赠与柳亚子。【作品赏析】这是一首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赞美新中国民族大团结的史诗,是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始的雄伟钟声。全词首先从联欢晚会的热烈景象触景生情,联想到旧中国的悲惨情景;然后笔锋转而颂扬国庆晚会上的浓烈气氛,喻示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共创繁荣局面的美好前景。上阕是对旧中国长期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批判。“长夜难明赤县天”,赤县神州千百年来陷入暗无天日的黑夜中,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这黑夜何时是尽头?谁能拯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声慨叹艺术地再现了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不甘屈辱不甘灭亡的心声,即使长夜难明,也要团结斗争,一个“长”字,一个“难”字,尽诉作者的沉重心情。“百年魔怪舞翩跹”,翻开血淋淋的近代史,从1840年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人民的苦难是空前的,既深受八国联军的侵略蹂躏,又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统治。这些“洋鬼”“土鬼”群魔乱舞,把中国的天空污染得更黑更暗。中国随着《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已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少数民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更是惨不忍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一起又一起屠杀、镇压少数民族的血腥事件,正是魔鬼横行猖獗,人民受苦遭殃。中国的悲剧已到了顶点,人们的怒火与反抗呼之欲出。“人民五亿不团圆”,在这样的现实中,各民族四分五裂,过不上安定的生活,五亿中国人不能团聚在一起。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割据,中国的大好河山已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国已不国了。再加上日占区“抢光、烧光、杀光”的残害,国统区捐税繁重、特务横行、物价高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情状之悲惨,难以穷尽。虽短短三句,却已把旧中国的黑暗、苦难艺术地再现出来,使我们更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各民族人民应携手并进,共创祖国美好未来,只有国家强盛了,人民才会“团圆”。下阕,诗人的思路返回到了眼前盛典上的欢乐场面。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国庆节,表现出了人民欢乐、祥和、幸福的新生活,展示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景。“一唱雄鸡天下白”,是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倒装。雄鸡一声长鸣,报道中国大地已经天亮了,而“唱”字更高亢、激越,仿佛是从人们心底喷出来的激情,道尽了人们摆脱漫漫长夜、迎来红日曙光的欢乐心情。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是伟大的,从建立工农武装,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昂首看天,觉得天格外晴朗,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万方乐奏有于阗”,各民族在祖国的生日大典上奏起欢乐的乐章,这其中包括新疆儿女的甜美歌声。这一句词写各族人民歌颂中国革命的胜利、歌颂新的生活,使我们想象到新中国百废俱兴、人民安居乐业的美丽画面,于阗之歌只是这幅长卷上的一角。由此我们更可以想到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盛况、举国欢庆的良宵盛会、新中国开创中国历史崭新局面的亘古奇观……所有这一切,怎能不让诗人灵感泉涌,欣然命笔呢!“诗人兴会更无前”,这里的诗人不仅指柳亚子,也指诗人自己,更泛指全国的文艺工作者,诗人的兴致是以前所没有的。一方面说明诗人应感知新生活、歌颂新生活,是对包括柳亚子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的肯定与勉励,另一方面说明诗人坚信未来的中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伟大和壮丽,坚信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安定团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首词上下两阕巧妙运用对比手法,极其鲜明地写出了新旧社会天上人间的反差。上阕写旧中国,下阕写新中国,而上下两阕又互相呼应,作者以旧社会的黑暗反衬新社会的“天下白”,以群魔乱舞反衬各族人民的欢庆歌舞,以旧社会的四分五裂反衬新社会的民族大团结。这样强烈的对比不能不震撼人心。【作者简介】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遗体在北京天安门水晶棺内。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主要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毛泽东诗词》(共43首)。